我于1964年8月畢業(yè)于貴州工學(xué)院化工系有機(jī)合成專業(yè),屬化工部統(tǒng)一分配到保定電影膠片廠(中國樂凱集團(tuán)公司前身)工作。至2005年離開工作崗位,工作41年。
前20年搞科研,在研究所從事彩色電影膠片配方研制、生產(chǎn)和質(zhì)量改進(jìn);
之后調(diào)生產(chǎn)單位,從事膠片生產(chǎn)和管理10年;
其余11年,從事質(zhì)量檢驗(yàn)、質(zhì)量管理工作。
我的一生中從22歲—63歲,我的青春年華、我的中年壯年,都投身于樂凱事業(yè),現(xiàn)年76歲的我,回顧這段工作經(jīng)歷,心中泛起對(duì)樂凱的無限眷戀和深情,如果要詳細(xì)記錄這41年的樂凱情結(jié),可能內(nèi)容太多、篇幅太長,我想以幾個(gè)節(jié)點(diǎn)來表達(dá)我的樂凱情愫。
一.文革中搞科研 生產(chǎn)
1966年我在研究所彩色片配方組工作,主任程樹楠,組長王蘭,組員石鍳、于忠良、張秀茹和我。文革初期一夜之間大字報(bào)鋪天蓋地,研究所四層樓的樓梯、走廊貼滿了大字報(bào),大樓外的樹與樹之間拉上繩子也掛滿了大字報(bào),人們也不工作也不搞科研了,都去看大字報(bào)了,不看還不行(大字報(bào)內(nèi)容就不談了),工作、科研處于半癱瘓狀態(tài)!知識(shí)分子自然也就成了“臭老九”,是被批判的對(duì)象。
不久“臭老九”們,下放廠部“五七干校”,從研究所下放的“臭老九”們不準(zhǔn)進(jìn)研究所大樓,有一件小事記憶猶新,“臭老九”們勞動(dòng)一天,汗流浹背允許在下班前一小時(shí)去洗澡,路過研究所樓下,程樹楠在樓下一個(gè)個(gè)叫,“王蘭、石鍳、于忠良…..我毛巾忘在樓上了,幫我丟下來”,他本人就不敢進(jìn)樓去拿毛巾,待我們洗完澡路過研究所大樓時(shí),他還筋疲力盡坐在臺(tái)階上說:“他們可能都在暗室聽不見”。之后,來了一位男“臭老九”說:“用我的毛巾快洗去吧”,總算解決了問題。
廠部“五七干校”在老1號(hào)機(jī)的舊廠房內(nèi),除了勞動(dòng)就是學(xué)習(xí),“臭老九”們按小組分配工種,如:有喂豬的、有做豆腐的、有植樹的、有做環(huán)衛(wèi)工作的……。學(xué)習(xí)當(dāng)然是有關(guān)文化大革命的文件、資料、自我批判及寫大字報(bào)……。相對(duì)比較,勞動(dòng)是愉快、輕松的,大家一邊勞動(dòng)一邊說說笑笑;學(xué)習(xí)就有壓力了,得用心領(lǐng)會(huì)精神,尤其是自我批判、寫大字報(bào)簡直就是一種負(fù)擔(dān)……。當(dāng)時(shí)的“臭老九”們是看不到自己的命運(yùn)和前途的,“五七干校”要呆多久啊,還能回到工作崗位嗎?誰也不知道,迷迷瞪瞪的熬日子。
作為我——當(dāng)時(shí)畢業(yè)不久的大學(xué)生,很想回到研究所搞科研、做實(shí)驗(yàn),但不可能啊!無奈且迷茫……。
言歸正傳,突然有一天通知一批人回研究所工作,我是其中之一,得到通知的人自然內(nèi)心興高采烈,但這種情緒只能隱藏在心中,表面仍然平靜如水;未得到通知的人自然內(nèi)心翻江倒海,這種情緒也只能隱藏在心中,表面依然平靜如水,但卻看到了希望,也許會(huì)分期分批回到工作崗位,但愿下批有自己。
回到研究所才知道,因八個(gè)樣板戲必須用國產(chǎn)彩色電影膠片制作,立即調(diào)回科研人員進(jìn)行研制,這是政治任務(wù)必須按時(shí)完成,越快越好,突然增加了思想壓力但心情卻是愉快的。
開始只是幾個(gè)人搞水溶性彩色底片、彩色正片的研發(fā),隨著工作量的增加,搞配方的“臭老九”也陸續(xù)回到研究所,分小組進(jìn)行彩色底片、彩色正片、彩色中間片、彩色反轉(zhuǎn)片的研發(fā)工作。
各小組成立后,小組長必須是工人稱為“參沙子”,即在知識(shí)分子中加入工人階級(jí)。
我當(dāng)時(shí)分配在彩色正片組,組長趙恒祥(工人),組員許吉林、詹先琦和我(均為知識(shí)分子)。
各小組人員都不多大約4、5個(gè)人為一個(gè)研發(fā)小組,為了提高工作效率每天都自覺地工作到晚上10點(diǎn)左右,有時(shí)還需要到半夜甚至凌晨,只要工作需要加班加點(diǎn)沒人計(jì)較,毫無怨言,大家心里裝的都是工作。實(shí)驗(yàn)的過程往往都比較長,在3、5個(gè)人的小組內(nèi)分兩班倒,每班工作10小時(shí)左右,有時(shí)需要就連軸轉(zhuǎn),一天除了幾小時(shí)睡覺及吃飯,都在工作,沒有人記工作時(shí)間、沒有人記加班時(shí)間,只要工作需要就全身心投入,絕不含糊,都年輕、身體好、頂?shù)米。?dāng)時(shí)多半人員都是單身,吃飯多在廠里。
當(dāng)時(shí)組內(nèi)業(yè)務(wù)氣氛非常民主、和諧,討論工作時(shí)都暢所欲言,充分發(fā)揮每個(gè)人的智慧、能力,為了配方的組成成分及合理性,每個(gè)人都查資料、反復(fù)計(jì)算配方組成成分,將結(jié)果集中分析、對(duì)比,排列組合,群策群力優(yōu)化出最佳配方方案,再通過實(shí)驗(yàn)來驗(yàn)證,如果實(shí)驗(yàn)結(jié)果符合預(yù)想,需要反復(fù)驗(yàn)證幾次一致,才算成功;反之也要驗(yàn)證、確認(rèn)失敗。當(dāng)然,兩者在實(shí)驗(yàn)過程中心情完全是不一樣的。
工作在循序漸進(jìn)、緊張有序、全身心投入的過程中,基本遺忘了當(dāng)時(shí)社會(huì)還處在水深火熱的文革運(yùn)動(dòng)中,廠外派系林立、武斗熱火朝天(保定是全國聞名的武斗重災(zāi)區(qū)),時(shí)有在武斗中獻(xiàn)身、流彈進(jìn)入家中的消息傳入耳中,幸運(yùn)的是中央英明果斷,早派防化兵對(duì)工廠進(jìn)行了軍管、8341部隊(duì)警衛(wèi),確保了廠區(qū)安全。我們才能無后顧之憂、安心工作。雖然當(dāng)時(shí)社會(huì)上文革如火如荼,保定電影膠片廠的廠區(qū)內(nèi)猶如世外桃源,無武斗、安全、正常、有序,讓人安心、踏實(shí)。
但廠區(qū)內(nèi)還是有派系,文革還在開展,雖無武斗卻有文斗,大字報(bào)、批判會(huì)、專案組仍有,但每個(gè)單位、車間都有軍代表,密切注意著各單位的思想動(dòng)態(tài),研究所的軍代表是趙**。軍管會(huì)一把手卞克強(qiáng)主任、軍管會(huì)劉振平副主任,他倆經(jīng)常到我們小組來,聽我們討論工作、分析曲線等等,久而久之他們也能說出點(diǎn)道道來。
當(dāng)時(shí)化工部也非常重視彩色片攻關(guān),部里經(jīng)常派侯國柱、朱光偉來我們小組詢問和檢查工作進(jìn)度,大家混得很熟將侯國柱叫侯專員,他也欣然接受。
突然有一天實(shí)驗(yàn)室門上貼了一張大字報(bào),內(nèi)容:”只低頭看曲線,不抬頭看路線” ,當(dāng)時(shí)被叫做“臭老九”的知識(shí)分子,猶如驚弓之鳥、膽戰(zhàn)心驚、低頭不語,一幅等著接受批判的心態(tài),恰在此時(shí)卞克強(qiáng)主任到來,看了大字報(bào)一揮手扯下、撕碎,丟進(jìn)垃圾桶,說:“誰寫的來找我”,并對(duì)大家說:“沒事,干你們的”。頓時(shí)“臭老九”們,如卸負(fù)重、輕松自如,心中吃了一顆“定心丸”。自然工作更加努力、勤奮了,再也不受外界干擾了。
配方研制在實(shí)驗(yàn)室過程中需要進(jìn)行:乳化、一成熟——水洗——二成熟——冷藏——熔化——加入涂布補(bǔ)加劑——涂布——膠片整理(裁切、打孔)——膠片應(yīng)用檢驗(yàn);其中每個(gè)步驟都有相應(yīng)的檢驗(yàn)和標(biāo)準(zhǔn),達(dá)到要求指標(biāo)方能進(jìn)入下一步。最后一步膠片應(yīng)用檢驗(yàn),需要洗印加工出拷貝。
當(dāng)時(shí)廠里沒有洗印加工設(shè)備,故膠片應(yīng)用檢驗(yàn)需要到相關(guān)單位進(jìn)行,如:北京電影洗印廠、八一電影制片廠、上海電影技術(shù)廠、西安電影制片廠、珠江電影制片廠、峨眉電影制片廠等單位配合進(jìn)行膠片應(yīng)用檢驗(yàn),來來往往大家都很熟悉了。應(yīng)用檢驗(yàn)中會(huì)發(fā)現(xiàn)一些問題,返回廠時(shí)帶回拷貝及問題,再診對(duì)問題進(jìn)行試驗(yàn)改進(jìn),再送相關(guān)單位進(jìn)行應(yīng)用檢驗(yàn),如此反復(fù)進(jìn)行直到應(yīng)用單位認(rèn)可。方可中試放量生產(chǎn),中試產(chǎn)品再送相關(guān)單位進(jìn)行應(yīng)用檢驗(yàn),直到認(rèn)可。才能到生產(chǎn)車間進(jìn)行小批量生產(chǎn),再逐步批量生產(chǎn)。
水溶性彩色電影正片歷經(jīng)了由實(shí)驗(yàn)室小試——中試——生產(chǎn)車間過渡(試生產(chǎn))——小批量生產(chǎn)——批量生產(chǎn)全過程。
在生產(chǎn)車間過渡(試生產(chǎn))之前,生產(chǎn)配方必須經(jīng)過廠生產(chǎn)科組織配方組科研人員、生產(chǎn)單位進(jìn)行匯簽,即科研人員需提供配方組成、特點(diǎn)、需用原材料及工藝要求;生產(chǎn)單位需確認(rèn)車間工藝、設(shè)備是否符合配方要求,雙方認(rèn)可后,需生產(chǎn)科、配方組、生產(chǎn)單位三方匯簽,方可在車間過渡試生產(chǎn)。
在試生產(chǎn)過程中配方組人員必須到生產(chǎn)車間跟班生產(chǎn),一則確保生產(chǎn)過程中配方實(shí)施準(zhǔn)確無誤(包括工藝過程及操作、工藝參數(shù)及控制、原材料的種類及用量等等);二則及時(shí)發(fā)現(xiàn)生產(chǎn)過程中,出現(xiàn)的問題及需要配方改進(jìn)以適應(yīng)車間生產(chǎn)工藝的地方等等。
終于在上世紀(jì)七十年代初中國有了自己的彩色電影正片,首先用于制作八個(gè)樣板戲的拷貝。帶有政治色彩的科研、生產(chǎn)任務(wù)終于圓滿完成。之后國產(chǎn)彩色電影正片轉(zhuǎn)入生產(chǎn)、質(zhì)量改進(jìn)的重點(diǎn)工作中,也一度成為我廠的“吃飯”產(chǎn)品。
二.水溶性彩色電影正片—上世紀(jì)七、八十年代廠里的“吃飯”產(chǎn)品
水溶性彩色電影正片從上世紀(jì)七十年代初投產(chǎn)后,我們彩色正片小組又接受了研發(fā)油溶性彩色電影正片的科研任務(wù),隨著生產(chǎn)、科研任務(wù)的增加,小組成員也增加并多次變化,除原來的詹先琦和我還在小組之外,又增加了齊玉山、張迎祥、***、高淑珍、張寶珍、張鎖榮等人。小組成員一方面搞油溶性彩色電影正片的研制:以水溶性彩色電影正片乳劑為基礎(chǔ),將水溶性成色劑更換為油溶性成色劑,其間主要任務(wù)是尋找溶解油溶性成色劑的有機(jī)溶劑及研制油乳的分散配方。另一方面還承擔(dān)水溶性彩色電影正片的生產(chǎn)和質(zhì)量改進(jìn)的任務(wù)。
隨著水溶性彩色電影正片的生產(chǎn)量不斷上升,隨之而來的原材料換批號(hào)的質(zhì)量鑒定、生產(chǎn)中遇到問題的解決、質(zhì)量的改進(jìn)和提高,有著大量的工作需要專人確保;同時(shí)油溶性彩色電影正片的科研任務(wù)也需要專人去做。在同一個(gè)小組內(nèi)承擔(dān)這兩項(xiàng)工作,就必然存在科研與生產(chǎn)、油溶與水溶交叉作業(yè),還有可能互相影響和牽制。根據(jù)現(xiàn)實(shí)的情況,研究所領(lǐng)導(dǎo)聽取了方方面面的意見,上世紀(jì)七十年代中期決定將一個(gè)小組分為兩個(gè)小組:水溶性彩色電影正片小組和油溶性彩色電影正片小組。
水溶性彩色電影正片小組:組長黃德敏 組員高淑珍、張寶珍、張鎖榮;
油溶性彩色電影正片小組:組長齊玉山 組員詹先琦、張迎祥、***。
水溶性彩色電影正片小組主要任務(wù):
1)確保車間正常生產(chǎn)、配合車間解決生產(chǎn)現(xiàn)場出現(xiàn)的質(zhì)量問題;
2)對(duì)生產(chǎn)配方進(jìn)行換膠、成色劑及原材料更換批號(hào)的質(zhì)量檢驗(yàn)、鑒定工作;
3)為配方改進(jìn)、提高質(zhì)量做儲(chǔ)備工作;
由于市場的需求量逐年增加,該品種的生產(chǎn)量也逐年提高,小組的成員也逐漸增多如:王磊、顧乃章、高波、寇慶林、夏柳燕等都陸續(xù)成為水溶性彩色電影正片小組成員。
當(dāng)時(shí)水溶性彩色電影正片成為廠里產(chǎn)量最大、盈利最多的生產(chǎn)品種,被職工稱為全廠的“吃飯”產(chǎn)品。
在歷年的同品種行業(yè)評(píng)比中連續(xù)奪冠,并多次榮獲部、市、省級(jí)優(yōu)秀產(chǎn)品稱號(hào)。
工作是繁重的、辛勞的,然而心情卻是愉快的,每天都忙碌著、開心著,干著自己愿意干的事,不計(jì)加班加點(diǎn),尤其生產(chǎn)車間需要時(shí),不管白天黑夜隨叫隨到,記得有一次半夜有人敲我家門,“黃工,車間生產(chǎn)有事,車間領(lǐng)導(dǎo)讓我?guī)?即用自行車馱我)到廠里去”。我隔著門說:“好,我穿衣服,你到樓下等我”,我下樓后就坐在他自行車后衣架上,他帶上我一直到生產(chǎn)車間門口,我直接就去了車間技術(shù)組,待處理完問題后,我說:“剛才是誰帶我來的,還帶我回去吧!”,大家笑了,說:“誰帶你都不知道,你就跟著走,半夜三更把你帶去賣了,你都不知道”,大家哈哈一樂!
還有一次,我愛人出差回來,等到晚上10點(diǎn)多,也不見我回家,就到廠里找我(當(dāng)年家里沒有電話,更沒有手機(jī)),到研究所一樓遇見馬延秀(研究所空調(diào)工,住在研究所一樓,夜晚就值班)就詢問我,馬延秀說:“都下班了,沒有人。你到2號(hào)機(jī)看看”。我愛人到2號(hào)機(jī)問門口值班人員,值班人員說:“看見她進(jìn)車間了,但在哪個(gè)崗位不好找,要不我去給你找”,我愛人說:“不用了,在車間就行”,便獨(dú)自回家了。其實(shí),對(duì)于我們的加班加點(diǎn)他也習(xí)慣了。這次是剛出差回來,等到很晚了不知我在哪里,故才到廠里去找。
上世紀(jì)七十年代中期,全國很多地方都建膠片廠,比較知名的如:無錫電影膠片廠、遼源電影膠片廠……等等,當(dāng)時(shí)稱為“兄弟單位”。為了協(xié)助這些單位盡快投產(chǎn),我受廠里派遣到“兄弟單位”幫助研制水溶性彩色電影正片配方,其后又多次到“兄弟單位”幫助解決生產(chǎn)問題。有的“兄弟單位”高薪高職聘請我,我婉言相謝,我怎么能舍得離開培養(yǎng)我的膠片廠呢?我對(duì)膠片廠有著深深的情感,如果我是一粒種子,膠片廠就是沃土。之后,二膠、廈門廠都相邀我前去,但我真的舍不得離開我深深扎根的沃土。
三.與技術(shù)引進(jìn)的新3號(hào)機(jī)結(jié)緣
1989年當(dāng)時(shí)我在膠片部,主管膠片部的乳劑、涂布、整理的生產(chǎn)管理、質(zhì)量控制、質(zhì)量管理工作及產(chǎn)品的質(zhì)量分析和總結(jié)。突然李玉堯副廠長找我談話,調(diào)我去新引進(jìn)的3號(hào)機(jī)工作,我沒有同意,之后又找我談話一次,告訴我這是廠部研究決定的,我仍然沒有去,并非我不執(zhí)行廠部的決定,而是因?yàn)?號(hào)機(jī)是技術(shù)引進(jìn)的新車間,工藝流程、設(shè)備都比1、2號(hào)機(jī)及老3號(hào)機(jī)先進(jìn),而且采用了先進(jìn)的計(jì)算機(jī)及自動(dòng)控制系統(tǒng),這些都是膠片部其它三個(gè)乳劑涂布車間無法相比的,我是文革前的大學(xué)生,計(jì)算機(jī)及自動(dòng)控制沒有學(xué)習(xí)過很生疏;更重要的是,當(dāng)時(shí)3號(hào)機(jī)組建選拔技術(shù)人員時(shí),都是要年輕的大學(xué)生,年齡都在20多歲,多半還是單身,而我當(dāng)時(shí)已經(jīng)47歲,不管知識(shí)結(jié)構(gòu)和年齡我都無法與朝氣蓬勃、欣欣向榮的年輕人相比,自我感覺無力勝任,婉約相拒。
沒有想到的是陳兆初廠長找我談話,向我講述3號(hào)機(jī)對(duì)于膠片廠發(fā)展、前途的重要性,并告訴我讓我去,并非要我在技術(shù)、生產(chǎn)上做多大貢獻(xiàn),而是讓我?guī)贻p人,讓他們學(xué)學(xué)老知識(shí)分子是如何工作的,看看老知識(shí)分子的工作態(tài)度和工作作風(fēng),我當(dāng)時(shí)覺得壓力更大了,知識(shí)、業(yè)務(wù)上不如年輕人,還要我?guī)麄儯@工作怎么進(jìn)行?作為一把手的陳兆初廠長已經(jīng)找我談了話,我心里清楚這事沒有回旋余地了。我只能表示那就試試看。廠長說讓我到技術(shù)組當(dāng)組長。我說技術(shù)組我去,但我不能當(dāng)組長,技術(shù)上我不如年輕人,我還要向他們學(xué)習(xí)。廠長表示理解,并說有什么問題可以直接找他。如此,我便硬著頭皮到了3號(hào)機(jī)技術(shù)組。
當(dāng)時(shí)3號(hào)機(jī)主任是馬少彬,技術(shù)組組長張靜,成員有張建恒、張弼時(shí)、楊華、譚晉、***、孫榮波、史秀紅,都是年輕的知識(shí)分子,其中孫榮波、史秀紅和我都是屬馬,可我比孫榮波大一輪12歲,我比史秀紅大兩輪24歲,其他成員年齡大都是20多歲的年輕人。
既然去了我就給自己定下原則,業(yè)務(wù)上必須向年輕人學(xué)習(xí),工作上仍按我的工作習(xí)慣和作風(fēng)去工作。當(dāng)時(shí)主任沒有給我安排任何工作,我沒有任何具體的業(yè)務(wù),于是我就自己安排先到各崗位學(xué)習(xí),一方面熟悉配方一方面熟悉操作,了解設(shè)備和工藝,遇到現(xiàn)場弄不明白的問題,我就回技術(shù)組向相關(guān)的技術(shù)人員請教,漸漸地我就與崗位操作工熟悉了,與年輕的技術(shù)人員也相處和諧,并向他們學(xué)習(xí)到很多新的知識(shí)和技能,也讓我很快掌握了新工藝、新技術(shù),幫助我適應(yīng)了工作的需要,大家在一起工作心情很放松、愉快、開心,我也漸漸忘記了年齡的差距,感覺自己也年輕了。我也非常感謝3號(hào)機(jī)的年輕人,是他們讓我的知識(shí)得到更新和提高,是他們讓我心態(tài)年輕化,回想這一段經(jīng)歷,還是很值得留戀的。
新3號(hào)機(jī)的工作是繁重的,承擔(dān)了三彩(彩色膠卷、彩色相紙、彩色正片)全部的生產(chǎn)任務(wù),三個(gè)品種輪流生產(chǎn),更換品種需要徹底做衛(wèi)生、檢查設(shè)備、儀表、電氣、空調(diào)系統(tǒng)維護(hù)、確認(rèn)等,往往只給一個(gè)班的時(shí)間(8小時(shí))。技術(shù)組更忙于配方分解、工藝參數(shù)制定、原材料備料、小量試驗(yàn)配合等等大量生產(chǎn)前的準(zhǔn)備工作。
生產(chǎn)順利,大家就按部就班各行其職。一旦出現(xiàn)事故或質(zhì)量問題,就必須全力以赴開會(huì)、討論、分析問題、尋找原因,生產(chǎn)處、配方組、車間技術(shù)組人員,必要時(shí)廠領(lǐng)導(dǎo)、總工也親臨現(xiàn)場,群策群力、充分發(fā)揮己見,或協(xié)商處理辦法或商討試驗(yàn)方案,技術(shù)人員都自覺跟班,工人有三班倒輪班進(jìn)行,技術(shù)人員必須在處理或試驗(yàn)過程中一跟到底,直到得出結(jié)果。自覺性都是在責(zé)任心的驅(qū)使下進(jìn)行,沒有人記加班加點(diǎn)、沒有人記報(bào)酬,這就是那時(shí)樂凱人的精神狀態(tài)、工作態(tài)度、工作作風(fēng)。
1991—1996年我從3號(hào)機(jī)調(diào)涂布分廠擔(dān)任副廠長;
1996—1998年我調(diào)公司質(zhì)量處擔(dān)任副處長;
1998年退休后返聘至2005年,離開工作崗位開始享受退休生活。
我今年76歲與樂凱結(jié)緣41年,我勤勤懇懇為樂凱事業(yè)貢獻(xiàn)了智慧、年華,無怨無悔;樂凱對(duì)我的認(rèn)同、首肯,我心存感激!
樂凱是我一生的惦念和牽掛,記憶是難忘而雋永的,不忘初心,祝愿樂凱事業(yè)永存!人生若有來世,我愿再與樂凱結(jié)緣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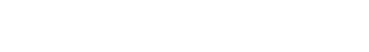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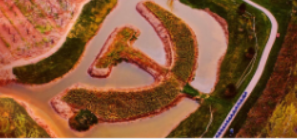



 0312-7923001
0312-7923001
